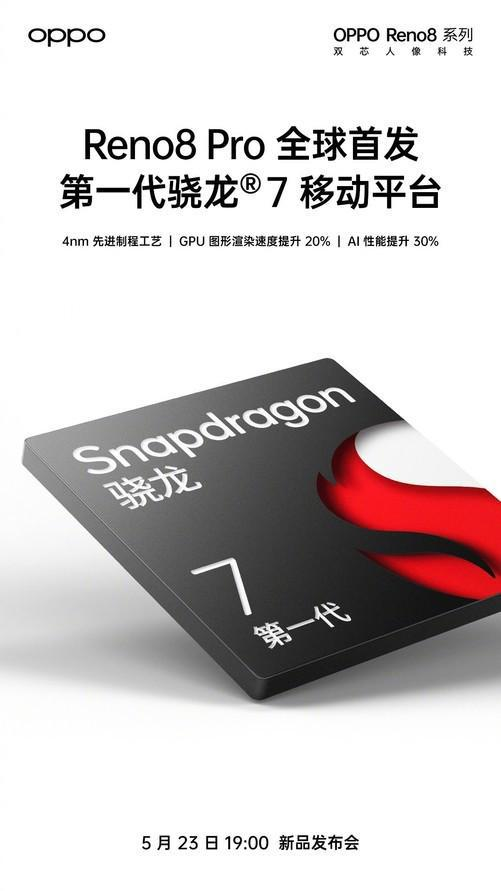李新奇整理稻種
袁老學生李新奇(右)向記者介紹最新研究成果
曹小平回憶給袁老理發的情景
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的試驗田
掃碼看視頻
□楚天都市報極目新聞記者 余淵 丁鵬 見習記者 胡迪凱 攝影:楚天都市報極目新聞記者 余淵 丁鵬 見習記者 胡迪凱
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進入5月下旬,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試驗田雖然還處于播種階段,未到稻禾開花拔穗時,但置身田邊,望著水塘與小拱橋,聽著蛙聲和鳥叫,也仿佛走入風吹稻浪的畫面。
只是,這樣的畫面里,那個萬眾追捧、不時會秀出兩句“袁氏英語”的幽默老人,再也看不到了。
弟子李新奇說,正對著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試驗田的一棟房子上,繪有老師袁隆平的巨型畫像,而那幾畝試驗田,則是老師生前最掛念的地方。
如今,在這處試驗田的田埂上,常常戴著一頂草帽下田的老人不再,但落日余暉下,工作人員剛剛栽下的一批秧苗,仍在靜待花開。
兩個心愿
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綜合實驗樓,袁隆平弟子李新奇的辦公室里,堆著大堆水稻種子。
對李新奇來說,每一粒種子,都飽含了老師的厚望。
如今,已成為第三代雜交水稻團隊負責人的李新奇,仍不敢忘記,一年前老師彌留之際,自己在榻前的承諾:要將雜交水稻事業進行到底。
李新奇說,老師生前有兩件事情放心不下:一是第三代雜交水稻如何突破更高產;二是雜交海水稻的研究推進工作。“我可以自豪地說,老師離開的這一年里,這兩件事都在不斷朝著更高更好的方向發展。”李新奇對極目新聞記者說。
2021年12月,由中國工程院院刊評選的“2021全球十大工程成就”出爐,其中“雜交水稻”工程與“洞察號火星登陸探測器”“極紫外光刻系統”“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等多項工程位列其中。評選詞寫道:“2020年,中國科學家團隊培育的第三代雜交水稻,創雙季稻畝產1530.76千克的新紀錄。雜交水稻的研發成功和大規模推廣,是世界作物科學與技術的重大突破,為全球糧食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海南三亞,雜交海水稻的研究推進工作也取得了可喜進展。海水稻又稱耐鹽堿水稻,是指能在鹽堿地生長的水稻品種。李新奇介紹,他們已經培育出耐鹽度達到1%的海水稻品種。
“今年我們優選了30多株海水稻,在一處靠近海岸的水域,栽種了40多天。”李新奇說。海水的含鹽度一般為3.5%左右,他們選取的水域,含鹽度大約為2.1%。雖然此次實驗還不能說明海水稻已經成功適應了在海水中的生長環境,但已是一次難得的嘗試與進展。
李新奇回憶,老師曾說過,我國的鹽堿地超過10億畝,如果能將其中1億畝開發種植海水稻,按最低畝產300公斤計算,增產的糧食就是300億公斤,可以多養活8000萬人口。“我們會努力向著老師所說的目標邁進。”李新奇說。
未曾離去
在袁老離去的一年時間里,李新奇有時覺得,老師似乎未曾真正離去。
過去一年,李新奇大多數時間泡在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和海南三亞南繁科研育種基地。它們一個是袁隆平生活工作多年的地方,一個是袁隆平生前幾個月長期停留的地方。“無論走到哪里,好像都能看到老師的影子。”李新奇說。
從家里出發到單位食堂,再到辦公室,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的試驗田,是李新奇的必經之地。
李新奇介紹,正對著試驗田的一棟房子上,有一幅老師的巨型畫像,而那幾畝試驗田,則是老師生前最掛念的地方之一。幾乎每天,他都要去看看試驗田,看看老師。有時,他看著試驗田,就會想起1983年,自己剛剛成為研究生,跟著老師一起下地干活的場景。那時,正是雜交水稻技術攻堅克難的關鍵時期,老師壓力很大,什么事情都要親力親為,身體非常消瘦。后來,老師逐漸上了年紀,大家都勸他不要再下田了,老師卻依然如故。
來自農村的陳媛菲(化名)是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的一名普通員工,她主要負責試驗田的犁地、栽秧等工作。雖然從未和袁老說過一句話,她對袁老卻并不陌生。陳媛菲說,在試驗田里,她見到袁老的機會比在單位其他地方大得多。現在袁老不在了,大家都非常想念他,“有時我在地里干活,感覺空落落的。”
和陳媛菲有同樣感覺的,還有袁老的“御用理發師”曹小平。
對于曹小平來說,袁老一直是她的精神支柱。2003年8月,為了掙錢補貼家用,曹小平在離家不遠的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后街,開了一間不到10平方米的理發店。
小店開業一個月后,穿著一件灰色T恤的袁隆平前來光顧。曹小平告訴記者,當時她一眼就認出了袁老。能給只在電視上見過的科學家理發,她既激動又緊張。讓她意外的是,袁老一點架子都沒有,還稱贊她理發手藝好,并說“以后會常來”。
袁老沒有食言。一來二去,曹小平和袁老熟絡起來。曹小平說,因為小店面積太小,而且位置偏僻,她曾萌生過遷店的想法。沒想到袁老很著急,隔三岔五就來找她理發,即使頭發壓根不需要打理,袁老也會讓她“做做樣子”。
在袁老的再三挽留下,遷店計劃就此作罷。曹小平守著這間小店,一守就是近20年。
延續夢想
“2020年11月30日,我最后一次給袁老理發。當時我們還約好,下一次理發在一個月后。”曹小平回憶。然而,后來她得知袁老在三亞摔傷的消息,她四處打聽,得到的答復是袁老病情不重。直到某一天,她從在湘雅醫院當護士的熟人處獲悉,袁老已經病得說不出話了,卻只讓護士幫他刮胡子,不讓人碰他的頭發。“聽到后,我心里好難過……”曹小平說。
2021年5月22日,袁老逝世的噩耗傳到曹小平耳中。她無法接受這一事實,暫時關了小店,把自己封閉起來。“那時候幾乎徹夜難眠。”曹小平說。目前,她在距老店200多米的位置開了一家新店,但老店仍原封不動。
“說實話,現在我也不知道該拿那家老店怎么辦。”曹小平說。如今,袁老的兒子經常到她的店里理發,但他們之間不會刻意提起袁老。她坦言,自從袁老走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她不敢踏入老店一步。去年11月30日,他和家人曾去袁老的安葬地祭奠。
“想袁老的時候,我就看看掛在店里的我和老人家的合影。”曹小平指著墻上的照片說。
在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從事雜交水稻研究工作30年的歐愛輝,也有著致敬袁老的方式。
歐愛輝說,自從1992年調入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她就一直跟在袁老身邊。第一次見袁老師時,她有些緊張。當時她是鄉農技站技術推廣員,丈夫在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跟著袁隆平工作。那一年,省里出了新政策,兩地分居的夫妻可以調到一個單位工作,于是她和丈夫一起找袁隆平簽字。聽完她的自我介紹,袁老說:“你們兩口子的情況我知道。兩地分居不容易,現在政策允許,我大力支持。”
后來歐愛輝才知道,當天袁隆平剛從國外回來,但是他沒有表現出一點疲態,而是十分平易近人。
多年來,袁隆平在實際工作中要求非常嚴格。歐愛輝印象最深的有兩次:一次是她將材料放在室內進行鑒定的時候,設定的濕度比袁老制定的標準溫度稍高,袁老檢查時狠狠批評了她;還有一次,她和同事用冷水灌溉調節變溫時,半個小時沒能達到預期的水溫,袁老再次嚴厲批評了他們,說他們對技術環境沒有控制好。
歐愛輝介紹,其實在生活中,袁老是個很風趣的人,業余時間喜歡叫上幾個人打一會兒麻將。平時大家陪他出差,他在路上也總能拋出各種各樣的話題,舒緩大家的情緒。
“我的心里面,總覺得袁老師好像還在,只是偶爾突然想到,已經好久沒陪袁老師打麻將了,這才想起袁老師已經不在了。”歐愛輝說。她的微信頭像是一幅稻谷滿穗的稻田圖片,她說,那是第三代大稻制種大田。袁老逝世已經一周年,她還在第三代雜交水稻課題研究組,繼續追逐著袁老的“禾下乘涼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