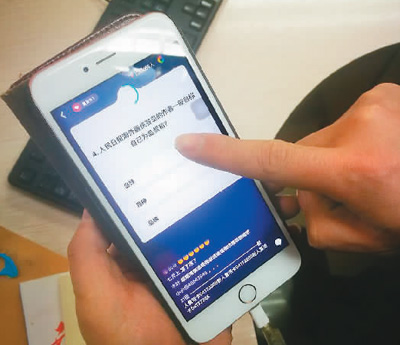 |
|
用戶在西瓜視頻“百萬英雄”直播答題活動俠客島專場答題。 |
“有560箱西瓜,每輛貨車一次運60箱,如果一趟運完需要多少輛貨車?”
“幾輛?幾輛?”今年20歲的天津高校學生馬劉松通過語音與微信群里的答友熱烈交流著。在10秒鐘時間里,他要從選項“8輛”“9輛”“10輛”中選擇一個正確答案。經過緊張討論,他選中了正確答案“10輛”,和近20萬人進入下一輪答題;而200多萬答錯的人只能退出或使用一張“復活卡”。最終,他成為15萬名答對全部12道題的一員,獲得20元獎金。
這是1月29日晚由西瓜視頻舉行的一場獎金達300萬元的“百萬英雄”直播答題活動,吸引了近260萬人參與。
2018年的新年鐘聲剛剛敲響,直播答題突然火遍中國,現實版“知識就是金錢”正在火熱上演。“沖頂大會”“百萬英雄”“芝士超人”“百萬作戰”……這些網絡直播答題活動的獎金動輒百萬元,場均用戶數也以數百萬計,僅1個月就成為中國最火投資風口。
這種模式是“風口”還是“一陣風”?在金錢喧囂中,如何把握好知識習得的進程?記者采訪了相關專家、學者、答友。
為啥突然火了寓教于樂名利雙收
江蘇一名女公務員在某直播答題平臺收獲101萬元大獎、廣州一名女大學生因為答對“以下哪位歷史人物被后人戲稱為慘王?”一題,力克近百萬名網友贏得103萬元獎金……近段時間以來,這些參與直播答題收獲百萬獎金的新聞在各類社交媒體迅速發酵,吸引人們廣泛關注。
艾媒咨詢今年1月份發布的《2017—2018中國直播答題熱點專題報告》顯示,在1月8日的直播答題大戰中,最高單場參與人數突破400萬,參與總人數超過700萬。目前,各互聯網巨頭支持下的直播答題平臺已達10多個。
直播答題為何突然火了?“它是移動端的綜藝節目《開心辭典》。”直播答題移動應用“芝士超人”公關部責任人趙媛媛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知識問答游戲早在十幾年前就已經在全球范圍內受到追捧。隨著4G網絡、智能手機、WiFi的極大普及,如今這種形式被搬到手機上,用戶只需一部手機即可參與,參與門檻低,再加之題目內容有趣、形式新穎、獎金額度高,自然迅速躥紅。
移動交互形式創新和巨額獎金制度,的確讓傳統的知識問答游戲發生了根本蛻變。
在“知識就是財富”“我不是在玩游戲、是在學知識”的心理預設下,加之巨額獎勵刺激,很多答友十分樂意參與。馬劉松如今參與直播答題已經3周,收獲了1300多元。拿獎金是他的主要目的。他表示,參與答題后,自己對一些常識現在能立刻反應過來,很多題目基本能記住。他同時說,“我和寢室同學組隊答題,比一起玩游戲好多了。”
也有一些答友并非為錢而來。今年49歲的教育工作者天劍(網名)參與了1個多月,最多時一天玩3場,已經收獲100多元。“我玩直播答題不是為了賺錢。”他總結了3個原因:一是將其看作一種知識檢驗手段,讓自己多年積累的知識有用武之地;二是通過戰勝同時在線答題的網友,獲得心理成就感;三是通過團隊協作答題,促進交流。他說,對于一些不會的知識點,他會去查資料,增加了學習興趣。
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博士生張華麟參與了4個平臺的直播答題,已收獲幾百元。他表示,目前直播答題題面涉及很廣,除了數學、物理、中華傳統文化方面的“硬知識”,還有緊跟時事熱點的“軟知識”,甚至娛樂行業明星個人信息都可能成為“考點”。“在知識的沉重與娛樂的刺激間尋找平衡,或許是眾多直播答題平臺在題目設置方面的目標。”
趙媛媛表示,“芝士超人”本著大眾參與、全民娛樂宗旨,鼓勵用戶調動身邊的親朋好友共同參與、共同答題,“通關”后不僅個人能夠收獲親朋好友贊許,還能獲得獎金、學到新知識,這就是常說的寓教于樂、名利雙收。
內容短板咋補知識變味舍本逐末
1月30日,被譽為直播答題“先驅”的“頭腦王者”微信小程序,因違反《即時通信工具公眾信息服務發展管理暫行規定》而被暫停服務,引發社會關注。題目中出現不良內容是其暫停服務的主要原因。無獨有偶,今年1月14日,北京市網信辦就“百萬贏家”直播答題活動將香港、臺灣作為國家列入問題,依法約談花椒直播相關負責人,責令全面整改。
除了出現政治問題,直播答題中某些題目胡拼亂湊、出現“肉夾饃原產地為江蘇”等技術性錯誤、聚焦某位明星信息等問題,都遭到網友吐槽。
在直播答題其勢洶洶的“撒錢”活動中,內容、知識如愿被推到前臺,同時也容易因此出現異化,變了味道。
“與其說直播問答題目涉及的是知識,不如說是一種娛樂的麻醉劑。”中國傳媒大學電視系教授劉宏對本報記者表示,直播問答涉及的知識習得,和人們傳統形式的知識系統、對知識的批判等不符,它將知識停留在一種取消了嚴肅性的層次上,“只帶有知識的部分元素,但改變了知識的方向和意義。”
劉宏表示,他的學生曾做過相關測試,很多參加知識問答電視比賽的選手,在賽后無法記起自己背誦過的百科知識。“這說明,學知識并不是人們參與知識游戲的目的,這種知識也注定進入不了社會流通系統。”
北京大學新聞學博士生靳戈對此十分認同。他認為,無論是電視百科知識問答還是如今的直播答題,更多是一項娛樂活動。“觀眾或答友通過參與,在羨慕、嘲笑和比較之間獲得了一種精神滿足,至于節目中有哪些知識已經不重要了。”
“想通過答題獲取知識確實有些掩耳盜鈴。”今年25歲的公務員徐言余表示,由于題目設置不科學,很多題目起不到學知識的作用。同時,現在時間十分寶貴,與其搭上半個小時學習一點碎片知識,不如系統地讀書,完整構建個人的精神世界和思維方式。網友“拖地哥”也認為,直播答題需要普及有效知識。
如果直播答題平臺只看到流量和廣告而非內容,當答友的興趣集中于獎金而非知識,這種模式將難以持久。因為直播問答的核心之一是內容,如果內容本身沒有吸引力,平臺與用戶之間就缺乏更多互動,難以達到沉淀用戶的目標。
劉宏認為,人類互動與知識層次有關,越是觀點、思想越需要互動,相反基本信息往往缺乏互動。由于資本對知識互動不感興趣、不愿意介入,目前很多新媒體將知識、觀點進行信息化、平面化處理,回避了較為深入的互動,這是需要注意的。
還能持續多久守好底線堅持創新
這場“燒錢”還能持續多久?當資本退場,還能留下什么?各方對于直播答題模式的這些擔心,源于對其盈利模式的擔憂。
目前,直播答題的資金輸入主要源于風險投資和廣告贊助。有業內人士建議,通過直播打賞、游戲充值、知識付費等方式,實現直播答題的流量變現。
趙媛媛表示,除了承接廣告,“芝士超人”將通過創新內容輸出、優化游戲形式,用知識、信息、內容搭建起文化、經濟與大眾之間的橋梁。她舉例說,未來會設置如“扎染”等傳統工藝題目,并在平臺中展示相關產品或將相關產品作為獎品,促進文化傳承和文化變現。
為迎合人們的知識興趣點,一些直播答題平臺還推出了“人民日報客戶端專場”“微信公號俠客島專場”等細分的答題活動。靳戈表示,作為大眾文化產業新模式,直播答題應以優質內容換取用戶注意力,以用戶注意力吸引廣告投放。他分析說,文化產業中有一個悖論,越是規模化生產的產品,越不具有藝術價值;越具有藝術價值的物件,越難以規模化生產。知識付費模式探索是實現“小眾文化產業”模式平衡、長遠發展的基礎。因此,直播答題付費模式需要探索、創新和堅持。
此外,直播答題的野蠻生長,是否將迎來相關部門的嚴格監管?
“讓人們快樂但不沉溺其間,既提供一種休閑方式又不是放縱的手段,這應該成為直播答題行業的底線。”靳戈建議,直播答題的知識點不能太難,但要足夠吸引人;形式可以娛樂,但不能觸碰社會公序良俗的底線。
“對于新生事物,我們要保持定力和耐心。”劉宏表示,政府要平衡好市場發展和政策引導之間的關系,既要防止資本控制可能帶來的異化,又要注意政府監管可能引發的“一管就死”。他認為,直播答題從觀念上對知識傳播、內容付費、知識游戲等方面的理解和實踐有所突破。他舉例說,對于交通法規宣傳、民生政策宣講等傳統宣傳活動,直播答題參與其中既有經濟效益,又有社會效益。
直播答題的興起,一個更重要的意義是引發人們對知識的社會意義和功用的探討。長期以來,無論是思想界、知識界還是社會大眾對此的討論都是不充分的。
“這種討論很有必要。”劉宏認為,如今隨著人們碎片化時間增多,知識習得過程也變得碎片化。媒體、課堂、官方引導等構成的社會知識傳播系統中,受眾學習狀態不同,也決定了群體性學習方式如依靠答題獲取知識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是有價值的。同時,知識和信息的區別如何厘清、個人知識系統如何構建、政府在社會知識傳播系統中的作用如何體現……這些問題都需要引起足夠重視。
“應該借助直播答題這個契機,不僅讓人們對知識有一個重新認識,讓學知識輕松起來,更要讓人們對碎片化知識和系統性知識習得的認知有一個根本性轉變。”劉宏說。
(本報記者 彭訓文 感謝本報記者張一琪、張遠晴、申孟哲對本文提供的大力支持)
這些年,我們經歷過的知識問答節目
2018年,開年大火的是直播答題節目。一場網絡直播答題,能夠吸引超百萬人參加。其實,在電視稱王時代,這種形式的知識問答節目層出不窮。
源起上世紀80年代
中國最早的知識問答類節目出現在1980年。當時,廣東電視臺率先推出《“六一”有獎智力競賽》。1981年,中央電視臺開始舉辦《北京中學生智力競賽》。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電視益智類節目開始盛行,如中央電視臺的《法律在身邊——“二五”普法特別節目》、地方臺的《民族知識競賽》、《規范用字用語知識競賽》等。
找到知識性和娛樂性平衡點
隨著湖南衛視《快樂大本營》開播,中國的綜藝節目迎來快速增長期。在這些節目中穿插的知識競猜,讓知識問答開始回暖。
2000年,《三星智力快車》在央視開播。這是一檔評價很高的知識問答節目,深受觀眾喜愛,尤其是青少年喜歡。同樣在2000年,《開心辭典》開播。《開心辭典》是一個面向大眾,使用大眾化題材的知識問答節目。很多人對此都有記憶,尤其是對王小丫、李佳明兩位主持人。兩檔節目都找到了知識性和娛樂性的平衡點,這也成為它們能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央視還有一檔與《開心辭典》齊名的節目,就是1998年開播的《幸運52》,主持人是李詠。這同樣是一檔益智類知識問答節目,通過競猜最后獲得砸金蛋機會,觀眾尤其對最后砸金蛋的環節印象深刻。無論是《三星智力快車》《開心辭典》還是《幸運52》,都是采用參與者與主持人對壘的模式。這是中國知識問答類節目的一種固定模式,也是一個時代標記。
觀眾對抗增加節目觀賞性
這些年,受到觀眾關注的知識問答節目是江蘇衛視的《一站到底》。每期參加節目的有11人,分為10位守擂者和一位挑戰者。他們年齡、身份、文化層次各異,其中守擂者手中都有不同價值的獎品,而挑戰者將通過20秒限時答題與守擂者一一對壘。在制作上,《一站到底》打破了《開心辭典》模式,采用觀眾對抗,增加了節目觀賞性。
隨著季播節目興起,知識問答類節目也開始走向季播方式。代表節目就是央視去年推出的《中國詩詞大會》。此外,央視最近幾年相繼推出過《中國成語大會》《中國謎語大會》《中國漢字聽寫大會》,這些節目專業性強,參與度廣,同時還能向全社會普及傳統文化知識,又有競爭性,一經播出在觀眾中都有較好反響。
移動互聯網助推全民參與
隨著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發展,問答節目開始在網上走紅。但移動端如何設計問答節目,吸引全民參與是一個問題。尤其是網絡具有匿名性、廣泛性等特點,如何保證節目公平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2018年剛過,微信推出游戲“頭腦王者”,讓微信用戶可以隨機進行對戰,題目由官方和用戶一起提供。
緊隨而來的就是網絡直播答題的火爆。在資本和技術的雙重推動下,網絡直播答題迅速打開了市場,吸引了巨大流量,也成為互聯網與電視的又一次“正面交鋒”。未來網絡直播答題走向何方,會產生什么影響,還要繼續觀察。(本報記者 張一琪)
直播答題是場“砸錢”大賽
經過一個月的“撒錢”之后,直播答題走入了一個瓶頸。
從原先只有一家“沖頂大會”,到“百萬英雄”、“百萬贏家”、“芝士超人”等多家平臺相繼進入,時間也不過是一周多。就在這短時間內,直播答題的“風口”已經擠滿了待飛的“豬”。
當然,擁擠的不光是撒錢平臺,還有為贏獎金趨利而來的數百萬網民。從原先幾百人分獎金,到如今十幾萬、幾十萬人分,雖然獎金從10萬元、20萬元飛速漲到100萬元、200萬元,甚至更多。但是越來越多網民感受到了競爭的殘酷,即使手握數張復活卡,親朋好友齊上陣,忙活半天,分到每個贏家手里的錢也只是“聊勝于無”。江湖中依然盛傳著一人贏得上百萬元獎金的傳說,但如今情勢下,這明顯成了掛在驢子眼前的那根蘿卜——看得見,拼命跑,夠不著。
有人說,直播答題很好啊,既長知識,還能賺錢。但這種零敲碎打的知識點,對一個人智慧成長明顯助益無多。其實,沒必要給直播答題太多價值附屬,這就是一場砸錢的裝機量競賽。
有統計顯示,互聯網時代,獲取一個時刻活躍、愿意互動的用戶成本大概是6元,甚至更多,而以一個100萬元獎金的直播答題場算,200萬人參與,平均到每個活躍用戶上,需要成本只有0.5元。這一輪砸錢下來,相關答題平臺下載量(即“裝機量”)無疑獲得了“大豐收”。
任何一個事物的興衰,都有一個邊際效用遞減。這不僅是錢多錢少問題,主要還是看整個中國互聯網直播市場的用戶池子到底有多大。經過一個月持續的高頻度競爭,用戶池恐怕已經開發得差不多了。也就是說,用戶增量達到一個峰值之后,再砸錢進去沖下載量,恐怕成本要漲不少。
所以,進入下半場后,動輒百萬元的投入誰來負擔?直播答題的高流量面臨變現難題。有的平臺找到了廣告商,比如趣店大白車就給芝士超人砸了一個億的廣告訂單,京東、美團等公司也紛紛參與進來。但隨之而來的就是一堆廣告專場。有些題目直接生硬地廣告植入,一次兩次還行,沖著錢用戶就忍了,但如果頻繁出現,用戶體驗就會變差,很多用戶就會懷疑值不值得為只是“塞牙縫”的獎金來看一場十多分鐘的廣告。
因為,這些新進的用戶有著非常明確且功利的訴求,就是答題贏現金,但這種趨利本性支配下的用戶很難對平臺產生情感依賴,黏性極低。很多答題平臺原先的主業并不是直播答題。這一輪“砸錢搶人”的硝煙過后,有多少新用戶能沉淀下來,而不是匆匆過客或者僵尸粉,還是個未知數。
說白了,直播答題像是一個“暴發戶”,流量和用戶暴增并沒有帶來商業模式創新,從上半場的砸錢搶人,到下半場的廣告輸血,怎么看都是一個非常簡單粗暴的一錘子買賣。有人說,直播答題是一個“風口”,但也有人說這只不過是“一陣風”。無論是風口還是一陣風,對永遠浮躁不安的中國互聯網公司來說,賭一把不吃虧,畢竟誰都不想成為風口來臨前那只尚未準備好的“豬”。



